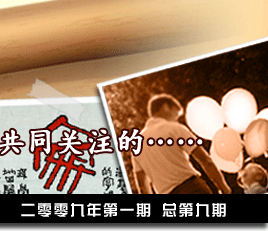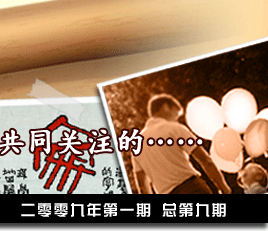感恩的心——家父百日祭
教研部 程进才
父亲程问喜,一生于乡间务农,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不抽烟不嗜酒,养育三儿一女均超而立之年后,于二零零九年正月初三下午不惊动任何人平静地离开人世间。
七十余岁的父亲身体硬朗,这么快的去世是我始料不及的,也是全村父老乡亲难以置信的。临终当天吃午饭时候,父亲还和村上的乡党打招呼,谈及我春节没有回家的原因,父亲自豪地讲:孙子今年中考结束以后回老家呆一个月。可惜父亲没能过完几个小时,更不用说等到暑假。我是家里的长子,平日对家事总有些感应,可这次我正悠然的从河北奔向北京准备购物,接到妹妹“你赶紧回来”的电话,小小的赛欧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到了150公里我也没有感觉到快。正月初四凌晨四时,看着安睡在灵床上的父亲面覆白纸,跪倒在灵堂前的草铺,伴随着长明油灯的闪烁,我竟然哭不出来。我回来看父亲的时间太少了,太少了。
父亲1938年出生于陕西朝邑县,二十多岁随三门峡库区移民迁至渭北旱垣,在知天命的年龄返回故里,一生奔走劳顿,命运坎坷孤独。我只是从乡邻的口里得知,我的爷爷早在五十年代就因为挑水跌入深沟丧命,悲伤的奶奶随后就去世。父亲排行老小,一个哥哥是哑巴,一个哥哥英年早逝,而已经成人的大哥和姐姐随着五十年代的三门峡库区大移民,远走宁夏贺兰县,多年杳无音信。沉默的父亲与子女的交流更是可怜到一年也没有几句话。父亲不识字,看不懂电视剧,他满口方言只有家乡人可以听的明白,在北京的日子里,每天从早到晚,父亲都喜欢一个人坐在床尾盯着雪白的墙壁发呆,在我家短短一周时间,我觉得父亲在快速变老。父亲拿到回家车票的喜悦,令我难以忘怀,父亲的快乐只有那块土地,那片禾苗。听妹妹讲,经过18小时的火车和6小时汽车的颠簸,父亲于傍晚5:00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上自行车去看看冬天的麦田。
盖房子的多少是检验一个农民成功与否的标志。父亲一生迁徙四次,可谓家贫如洗,但为自己为子女盖的正房超过1000平米,在村上算是成功的农民。渭北旱垣是一块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当地的俗语说:“龙山、马胡,渴死寡妇”形象地了反映了当地恶劣的环境,电影《老井》展现的场景依然无法阐释当地吃水的艰难。竟然在这个地方、在三年困难时期哑巴伯伯和父亲从窑洞走出来住上了全家第一座有砖有土的厦房;为了养家糊口,我跟随父亲寒冬腊月用架子车拉着1000多斤红薯,深夜11:00从家里出发,赶在天亮前到达县城批发给贩子,换得一个又一个10块钱,这样终于在1983年,随着我们姊妹四个的长大,父亲另立门户,盖起了第二座厦房;1987年随着移民返库,五十岁的父亲再次拉着架子车,驮着小麦或者玉米种子,奔走于家乡和库区之间,一个来回就是380里路程,路途沟壑纵横,沙丘遍布,大漠孤烟直的旷野中一个个茅草庵竖立起来,其中就包括我父亲为全家搭建的两个;进入二十世纪,父亲到了城里人已经退休的年龄依然劳作于田间,为了两个弟弟能够娶上媳妇,父亲第一次向自己的长子张口借钱,盖起来自己生命中最宏伟的两座二层楼房,正是这两座楼房压弯了父亲的脊背,但永远碾压不跨父亲的心。
父亲是天下最坚强的男人。俗话讲,人生的光景几节过,前辈子好了后辈子坏,后辈子好了前辈子坏,可父亲的一生中却没有舒心的日月。 一个不识字的男人在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开始挑起来家庭的重担,在农业学大寨时期顽强打拼着一个山村的梦想,在改革开放的岁月更是精心哺育着四个孩子逐步长大成人;二十一世纪,一个老弱病残的家庭在父亲的引导下平稳发展。我清晰的记得读小学时候,每逢周末都要帮父亲推车往返于百里外的县城卖红薯,伫立在国棉十三厂的大门口,寒冷的北风吹得我浑身打颤,父亲从内衣口袋里面摸索出皱巴巴的一毛钱让我去买油糕吃,而他自己则啃着又黑又硬的冰冷的红薯面馒头,静候工厂大门打开,那情那景影响着我的大半生。1992年冬季在我准备结婚的时候,父亲寄来100元钱,未婚妻当时就说给她买个银戒指吧,被我一巴掌扇了过去。当时萦绕在我心头的只有年迈的父亲用自行车驮着200斤红薯伫立在寒冬中的情景。儿子长大成人后,给父亲买了北京烤鸭,给父亲买了茅台五粮液,可父亲习惯自己“早上红薯煮,晚上煮红薯,想吃改样饭,就是红薯面”的岁月,到临终前依然是手捧大老碗,蹲在大门口吃那喷香的燃面。或许在父亲的记忆中,能吃上小麦磨出的白面就是最大的满足。
父亲没有上过学,不会读书更不会写字,但父亲读透了人生的大课本,用自己的行动写出了生命的碑文。跪在父亲灵堂的草堆上,答谢着来自异乡的父辈们隆重的祭奠,倾听着亲人们大声的哭诉。我再次体会一生为人忠厚,做事周全,苦着自己,照顾乡邻的父亲情怀。可能父亲早就预知了自己的寿日。这几年父亲先后带着卧床不起的弟弟四处求医,陪着两眼摸黑的母亲来京看病,为两个弟弟分别修建了一座院落,还打电话问我是否需要在农村买一个庭院。把家里人的事情安排停当后,父亲又分别去看望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去世前的两年时间里,父亲踩着电动自行车行程千里看望地处异乡异县的7个侄儿,5个侄女,3个外甥,还有曾经帮助过我家的一些人家的子弟;正月初二下午,当父亲的外甥来家看望父亲时候,父亲说出来了最后的安排,打算正月初九 去看望远在它县的瘫痪卧床的外甥女,可惜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也正是在这时候,我才得知,六十年代为全村上千口人造福的四十五丈深的井,竟然是父亲做生产队长时候与乡亲们挖掘的。那可是四十五丈,也就是说130米深的水井啊,正是这口深井在当时一直到今年还在供养我的故乡的人。
质本洁来还洁去,父亲走的十分坦然,没有病因,身边没有任何人,更没留下任何只言片语。我想,父亲把该做的事情都已做好,该说的话都已讲完,需要安排的事情都安排妥当,所剩下的都是他老人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 他把两个尚未成家的弟弟交给了母亲,他把因为SAS而瘫痪的弟弟交给了长子,他把 年老体弱且双眼模糊的母亲 放心的交给了我们。我今天终于明白,他在北京、在长子身边长长的舒的一口气的含义:他把家庭的重担留给了从未担过担的长子的我。
低微却崇高,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活了七十二岁,墓穴是用楼板盖的房子,在灵堂摆放到“头七”才安葬,亲朋好友无数人祭奠,出殡的当天,全村送葬的人从家里几乎排到了陵园。随着八抬大轿的起落,一个圆圆的土冢依照牌位添加到了祖坟的领地。按照习俗,下葬后三天每天都要“打怕怕”,为的是不让父亲一人在山坡上孤单害怕。冥纸和麦草燃起,灰屑如黑色的蝴蝶满天飞舞,我们给父亲说着话,让他安息,在这面向西南角的沙坡上有我的爷爷奶奶,有我的大伯,二伯,三伯,有我村更多的长辈,父亲是不会孤单的,也不必感到孤单,这面沙坡与他修建的那二层楼房没有阻隔,只有2000米左右的距离,他还是极容易来家中看看;我们兄弟姐妹永远忘不了他,会时常来探望他的;虽然我相距遥远,但父亲如影随形的在我身边。前几天刮大风,我还专门打电话给弟弟,为父亲的陵墓添加一扑黄土。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打开沉放了多年的茅台酒,跪倒在父亲的坟前,回忆着着父亲那永远慈祥的面容,任凭泪水顺着脸颊滴在父亲的灵口。当父亲为了五毛钱的学费从村上借了好几家的时候,已为人父的儿子才能读懂他的胸怀;当两个依然不识字的弟弟被别人骗走财物时候,父亲默默的表情铸就一生的无奈。
我想,父亲走了,或许是一种解托。父亲没文化,出门不多,不看电视,对于社会的变化了解更少。记得父亲在京照顾母亲,同病房的阿姨说到房子价值上百万的时候,父亲愕然,这是他根本不曾听过的钱数。晚上父亲在家里还专门跟我确认这个数字是不是听错了,当我回答自己的房子也值价百万的时候,父亲沉默了,他默然的想自己生活在农村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当家里的耕牛被窃贼偷走,父亲愤怒了,他唠叨到毛主席的时代,虽然生活苦一点,但心里是愉悦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他的向往;当国家说小麦涨价 1 毛钱,而化肥价格翻了番的时候,父亲失望了,他低头思索,这赖以生存的土地还能种点啥呢?不是父亲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今天,他老人家亲手播种的小麦已经金灿灿的沉甸甸的等待收割了,儿子在遥远的京城为他献上百日的祭文。父亲,您再也不必愤怒,再也不需要失望,再也不要惦记您那两个不识字的儿子了和陪您走过四十年的老伴,儿子彻底读懂了您无声的遗言。父亲,您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