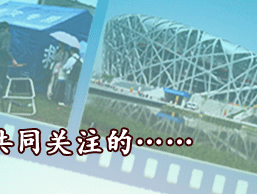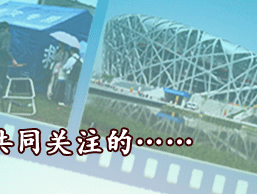我的2008——地震日记片段
片段一:5月12日
下午在海淀区的办公室(16楼)上班。
14:33分,手机响了一声断了,一看是家里的号码,于是起身到办公区旁的过道窗户边回电话;信号总是不好,不通,奇怪。
面对白墙,忽然觉得墙体对我忽近忽远的晃悠,莫非坐久了站起来头晕?再往窗外看,还晃,胸口一阵难受,忽然反应过来——地震?
转身到办公区门口,同事们纷纷嘈杂:“地震了!还晃呢!”大家心理素质都很好,说了几句继续埋头工作,没人要撤离疏散什么的。
我回到窗口,继续打电话,没人接,有些烦,怎么就没人了?回座位,又打了一次,线路忙。
14:43分,手机再响,看是家里区号,赶紧接了,正想埋怨两句怎么不接电话,就听那边父亲很着急地说:“家里发生大地震了!震了五分钟,现在人在楼下院子里,房子没垮。”因为是用楼下杂货店的座机打的,等着用电话的人多,父亲没多说就挂了。
当时心生疑惑,我刚才感受到的难道是同一个地震?那该多大啊!震中在那儿?估计家里到北京之间,莫非陕西南部?
上网,搜索。
14:57分,联合早报的消息出来了:四川7.8级大地震,震中成都西北92公里处。
15:08分,电话响,号码陌生,以为是广告,没好气地接起来,对方说我是F,才反应过来是远在美国加州的妹夫。他说刚知道四川地震了(小妹在东海岸正是熟睡时间还不知晓),打家里电话又不通,很担心。赶紧告诉他家人都没事,让小妹放心。
网上消息陆续出来了,四川汶川7.6级大地震(后来又说核实是7.8级),其余情况等更多的消息吧。家里距离震中估计三四百公里,电话线路瘫痪了,具体的情况不清楚,还是有些担心。
传言北京有4级余震,朋友们都在相约晚上不回去,我想想觉得不可能,决定照常回家睡觉。快下班的时候官方出来辟谣,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其实北京距离震中千里之外,真没必要风声鹤唳。
片段二:5月14日
这两天心里很难受,虽然家中只是受了惊吓,基本没事,但看到灾区的情况报道,胸口就堵得慌。
一遍遍在新浪看最新的消息,眼圈润了一次又一次。
很多久未联系的朋友,都在这几天纷纷给我电话和短信,询问家中情况——家里平安,多谢大家!
登录到同学录论坛,看到成都同学上来报平安的帖子,说当时的绝望不堪回首。
身边的朋友有献血的、申请当志愿者的、有的是医生已经奔赴灾区的……从总理到武警军人、医护人员,大家用命在救人——向一线所有的救援人员致敬!没有出过一分钱、一丝力、献过一滴血却在指手画脚说空军不及时、地震局不预测之类的看客,请闭上你们的嘴巴!
刚刚接到妈妈的邮件,说当时地震的几分钟内比一个世纪都要长,因为不能抛下行动不便的外婆,她和爸爸都没有往外跑,而是手拉手在承重墙下坚持,人晃得快站不住,台灯等物件都哗啦啦往地下掉……如今只有余震,基本无事;停学的小表弟也将在明天复校;只是担心都江堰的故人至今毫无消息;信末叮嘱我要积极为灾区捐款。
好了,就说这么多,心情不好,外面下雨,如果灾区的雨都能下在这儿那就多下些吧!
片段三:5月15日
从家乡县民政局一朋友的网络日志看到的,转载过来:
“……昨天县上组织的募捐现场,场面十分感人。第一个来捐款的,是一名5岁的小女孩,由她父亲带着,捐了5元钱。不断有人走上来,投入自己的善款,还有不少人在收款开票处捐了钱就走,不留姓名,其中有500的,有1000的。感觉这次为“5·12汶川大地震”捐款,群众的积极性是历年来最踊跃的一次。因为大多数人都亲身经历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因为大家都在关注和关心着灾区的一切。那些异常惨烈的灾难场面,那些生死未卜的同胞兄弟,那些扣人心弦的救灾场景,始终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镇西镇组织的献血活动上,一位卖菜的老婆婆因为不够献血条件,就摸出50元作捐款。民富村,村民已自己出钱购买救灾物品,拉了一车又车。界牌镇,一位个体老板想捐赠10吨黄瓜,因不方便储存和运输,被我们婉言谢绝…… ”
片段四:5月20日
已经是第八天了,举国哀悼……昨日头七,在默哀的三分钟遥望故乡,曾经熟悉的山水和人们不知道成了什么摸样,心又一点点疼起来。
汶川,这个地名在这次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不知道它在四川阿坝州;但对我而言,却很是亲切。从小在阿坝山区的九寨沟县生活,那时候的汶川是阿坝州最好的地方(因为最接近成都平原),出了汶川,就叫“下山”了(汶川属于山区,和成都平原交界,也是板块的边缘地段,所以才是地震高发区),九寨沟退休的人大多选择在汶川和都江堰等地生活。
相比偏远的九寨,汶川的教育质量相对更好,05年回九寨的时候还听说许多比较富足家庭的才有条件送小孩去汶川读书(因为九寨沟的升学率极其低),至于能送到成都或者都江堰去的,更是优越的少数。
记得小时候从九寨沟到成都,需要坐整整两天车,一路翻山越岭,路旁就是高高的山崖,趴在车窗往下能看见山崖下翡翠蓝绿的水潭。因为晕车晕得一塌糊涂,也不知道害怕。那时候出山到成都,能选择的就是两条路,西线:九寨—松潘—茂县—汶川—都江堰—成都;或者是东线:九寨—平武—江油—绵阳—德阳—成都;曾经多次奔波在这两条路上……这次地震,随着电视里一片废墟的图像和遇难者的人数通报,这些熟悉的地名一一呈现,脑子里又浮现出它们原本美丽的模样,泪落无声。
那时候父亲在甘肃文县工作,经常出差去武都。我曾经跟在父亲身边生活过一年,每天去父亲所在的碧口水库下属的水文站玩,记得有条大大的铁鱼(用来测量水位的)是我又爱又怕的玩具。那些地方、那些地名,我以为都已经沉淀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了,但这次意外被翻将起来,却是以这种惨烈的方式:武都受灾,文县在预报6级余震,碧口水库发生位移……那些曾经熟悉的人们和山水,现在怎样?不敢想,不忍想。
四川山区多地震,西线的路上,有一处地震遗址,几十年前的大地震中,山脉沉没了,形成一个湖——叠溪。旅游团去往九寨沟的时候导游通常会提及,大家好奇的议论几声,也只是作为遥远的故事和旅途的谈资罢了。 76 年松潘大地震,妈妈正在九寨,感受了强烈的震感,但她说远没有这次猛烈和恐惧,尽管距离震中更远了二百多公里。至于我小时候,九寨的小震不断,洪水偶尔,倒是也慢慢习惯了。真正恐怖的是泥石流,见过的老人说好像大山裂开了,大石头和沙土如泥龙奔涌而下,瞬间就把河谷村庄填平了,就好像他们从未在这世界上存在过一样。后来离开山区,只感受过两三次震感,这次在北京感觉到,本来也没多害怕,但是第一时间得知四川家里也地震的时候,忽然后背发凉——两千公里之外都受影响,这该是多大的一次地震!随着消息的陆续传来,才知道后怕,才知道心痛,才知道这次遭受的是多么惨痛的灾难!
从网上知道户外朋友周六组织的一批衣物当晚就起运了,还有一人当志愿者跟车前去,而我认识的领队和两位朋友也参加救援队去了四川,真心佩服他们的高效率!
这三天是全国哀悼日,心情也很沉重。救援进入防疫和安置阶段,不久还需考虑灾后的重建。祈愿四川灾区的人民,一定要坚强,加油,四川!
片段五:5月28日
今天去四川当志愿者的几位户外朋友回来了,带来的一线感受:“自16日下午15时登上飞机,12天来数次进出地震灾区,感觉到此次救灾抢险的宏观布局恰似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学应用。救灾力量及时到位,防疫工作衔接紧密,移民安排有条不紊,灾后重建开始铺垫,民间志愿者插空补漏。存在的问题都在细节上面:物资分配粗放,平民救助及志愿者的心理准备不足等”。
这几位朋友在四处打了几天零工(当志愿者需要自己找活儿干,刚去的时候很不适应,他们曾经很怀疑自己去当志愿者更有意义还是在北京上班捐款更有意义),得知三江交通阻断需要药品,于是徒步翻山背包送药进去;再得知通讯阻断,返成都筹备后再进三江架设起了一台卫星电话,能支持两部电话两台电脑(成为三江信息传递的唯一路径,对救援工作起了极大保障,后来被媒体称为“绝地网吧”),留下一人做技术维护后,大家陆续返程。在架设卫星电话后,大家终于觉得此行四川还是有意义的。
片段六:6月16日
今天和家里通电话,得知阿坝州工作的小舅被派到映秀救灾,已经忙了半个多月了,条件很艰苦。他所在的九寨沟县没有受灾,要去州内的其他灾区帮助修建临时厕所,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回去。目前很担心映秀重灾区会不会有瘟疫等疾病危险。
另外得知表姐家当兵的大外甥也在救灾,一直觉得他还是刚参军的十八九岁的孩子,但这一次他们却是奋战在一线的主力,比想象的还苦还累,让表姐心疼不已。
片段七:11月11号
北京的秋天,气温渐凉,晚上和家中来京培训的同学一起吃饭,再次提到地震。同学在市总工会工作,说前几天才接待了阿坝州的同仁,他们从地震到现在忙了整整半年,才抽出点空去感谢市工会当初的捐款,也说了说灾区现在的情形,很困难。同学顿了顿,话语有些沉重:“我们不觉得了,但对灾区来说,地震还没有过去!现在他们什么都还没有,家没有, 亲人没有,冬天就快来了……怎么挺过去啊!”
忽然很内疚,只是半年时间,对地震的报道已经淡出了媒体的视线;汶川地震,也成为灾区外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年度盘点时的一件大事符号,或有或无的,我们都选择了遗忘。而真正的灾区呢?他们面临的是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切肤之痛,这种阴影在心底不是半年就能抹去的,而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也不是半年就能完成的,对他们而言,地震的影响远远没有过去……
后记:灾后的重建才刚刚开始,希望唐山的今天能成为灾区的明天,愿幸存者都能好好地、坚强地活下去,迎接那一天的到来。
|